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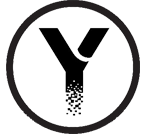
作者:杨燕迪 来源于:艺术起点
杨燕迪
-、引言
“知己知彼”。人们当然还记得中国人民那种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蒙昧闪境。正当中国人纷纷睁开双眼贪婪地注视西方(以及东洋)的大千世界时;正当文化界、知识界和学术界争先恐后地抢出、抢译、抢搬“舶来品”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这股“拿来主义”的高潮中,却有一个角落――音乐学――保持着持续的沉默。或许是音乐学在我国过于力单势薄了,或许因为音乐学在西方正高度发达使得我们难以一下子总体上去把握它。无论如何,事实情况是,音乐学界没有同音乐创作界、表演界及其他人文科学界一道加入这场“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洪流。学者们都明白,知识的进步与发展(音乐学即为音乐知识的体系建构)不能违背“知识国际共享”这一现代学术原则,否则这种知识不仅无法向外界传播,而且它的可*性和创造价值都是值得怀疑的。当一门学科在一种没有外界同类刺激的封闭状态中闭门造车时,这门学科的发展无疑是存在危机的。
当然,对危机的认识离危机的解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千镏校加谧阆隆薄1收哂?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87年10月赶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音乐系进修音乐学。西方音乐学者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这是笔者一直困惑的问题。这里笔者仅想为国内音乐学同行们打开一个小小的窗口,以期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并为修正我国音乐学的封闭状态做些有益的尝试。
二、概 观
本世纪六十年代,英美音乐学已进入全面的成熟期。也许正是因为成熟了,学者们才突然意识到需要静坐下来彻底澄清一下“自我”。音乐学是什么?音乐学已做了什么?它今后应该怎样?
196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音乐系主任、巴赫专家门德尔(A. Mendel)在纽约第八届国际音乐学大会上作名为《证据与解释》①的专题报告,这篇音乐历史元理论的专论一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196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美国的人文科学”丛书,旨在全面考察人文学科在美国的发展状况、成就及展望, 《音乐学》②被列为此丛书之一,由美国中世纪音乐学者哈里森(H.Harrison)、美国著名音乐学家帕利斯卡(C.Palisca) 和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胡德(M. Hood)共同撰写。该书不仅综合考察了音乐学的历史、在美国发展的状况,而且从音乐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音乐学整体的框架设计重新子以规定,对音乐学的元理论进行了重新阐发,出版后即引起广泛注意。
1965年,美国战后一代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克尔曼(J・Kerman)在《美国音乐协会杂志》上发表“美国音乐学侧影”③一文,指责美国音乐学界缺乏反思,缺乏价值判断和审美批评,呼吁音乐学从实证主义的死水中走出,向文学批评和美术批评*齐。
这场产生于美国并随后遍及整个英美音乐学界的反思浪潮自此后有增无减。对音乐历史哲学特别感兴趣的音乐学家特莱特勒(L.Treitler)自六十年代以来不断在各个音乐学刊物上一系列有关音乐历史元理论、音乐分析学元理论的论文,据称现正在编撰《音乐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一书;美国音乐史专家切斯(G.Chase)大力倡导“文化音乐学”(Cultural musicology)的建立,主张音乐学必须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和借鉴理论框架和建构;至于民族音乐学家对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只重“文本”(text)而忽视文本“外围”的研究方法的批评更是比比皆是。显然,音乐学自身范围内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它有“危机意识”,它正在做自身调整。
但是,让我们还是先回过头去追溯一下音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并考察一下它的现时状态,否则我们将无从比较,因而也无法把握这种自我调整的意义。
“音乐学”一词最早进入英语世界大约是本世纪初的事情。它的德文对等词“Musikwissenshaft”则早出现几十年。十九世纪末,在对这门学科进行第一次自身界定时德语学者的贡献是鹤立鸡群的。其中阿德勒(G. Adler)和里曼(H. Riemann)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虽然阿德勒和里曼在对音乐学的子学科进行具体归类划分上有差别,但二人都一致认为音乐学是一门包含一切音乐知识研究的严肃学科。它不仅涉及音乐的风格发展、人物评传、体裁及形式演化等“历史性”的研究方面,也包括美学、心理-生理学、比较音乐学等共时性的、聚焦式的所谓“体系性”的研究方面。理论的框架规定使得理论的发展有了赖以跃进的依托。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音乐学从一个本不太注意的或令人怀疑的(其它学者和音乐家同时对它持不信任态度――音乐学在英语世界刚刚萌芽时遭到了几乎同样的“白眼”)“业余嗜好”(许多音乐学者起先均是外学科的“业余份子”)稳步进入了大学的人文学院。阿德勒、里曼、施皮塔(J・Spitta)、克雷奇马尔(A・Kretzschmar)、古利特(W.Gurlitt)等一群泰斗人物撑起了音乐学的大厦。直到二次大战前,德语学者在音乐学界的统治地位是举世公认的。是他们拓展了音乐学的疆界,并规定了音乐学的实质。
然而,虽然阿德勒等人在理论上强调 “历史音乐学”与“体系音乐学”的并行发展,但在实践中“历史音乐学”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主导地位。阿德勒本人的研究中心是古典乐派,他所倡导的“风格批判”(Stylistic criticism)至今仍是西方音乐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由于音乐学从一开始使面临着浩翰无边的谱面与文字资料收集、整理的困难,因而学者们的主要精力便投向乐谱文献及文字文献的清查与出版工作中。从十九世纪初“重新发现”巴赫开始,音乐家中的历史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惊异巴赫之前还有许多只闻其名而不知其“音”的大师们(或既不知其名也不知其音的中小人物)。为了追溯音乐发展至今的逻辑线索,人们也必须把探索的长矛投向悠远的过去。中世纪格里哥利圣咏流传情况的模糊画面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文艺复兴的大师又一个个地“复活” 了。与之相平行,古谱学、古文字学、版本编订等一系列“生僻枯涩”的实证性子学科逐渐成了音乐学的重要内容。④
可以想见,德语国家对其他西方国家的音乐学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而英语国家在其特有的经验主义思维习惯的指导下,又将德国音乐学这种重“历史”、轻“体系” 的倾向推向了极致。德语国家在进行扎实的历史实证工作的同时,还一直保持着它固有的对元理论和抽象思维的偏好,因而音乐美学、比较音乐学、音乐社会学等“体系性”的学科仍保留着一席地位。而英美(尤其是美国)在一开始接受阿德勒“历史一体系”模式的时候便开始了对它进行经验主义式的改革。于是,音乐美学基本上让给了哲学家们,音响学重新又回到了物理学的领域中,至于社会学,至今仍是英美音乐学的薄弱环节。由此,当英美音乐学摆脱德国影响着力建立自己模式时,它又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建构。
在当今英美大学院校中,音乐系的学生主考方向一般分为音乐历史学、音乐分析、民族音乐学、作曲、演奏(唱)。撇开作曲和演奏(唱)这些实践性的音乐学科不论,音乐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包括musicology(音乐学)、analysis(分析)、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和十九世纪德语国家的“Musikwissenshaft”不同,“musicology”在英美大学院校中的公认含义是相当狭窄的:它几乎仅指西方艺术音乐传统的历史研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交响乐史、贝多芬研究等等。依照阿德勒的观点,西方音乐史主要是音乐风格的历史,它关心的焦点是音乐史中各种风格的相互影响、沿革和发展。而在弄清这条大线索之前,实际上许多“点” 的问题更加让人迷惑。事实上音乐学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考证个别人物、个别作品的外部确定证据上的;如考察某一十五世纪的经文歌的所有抄本,比较其真伪最,后提供一个可*的乐谱文本。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音乐语言的具体用法,判断这些用法的风格来源、特征,考察其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并将它归到一个大的风格范畴(时代风格、体裁风格等)中。在学术圈内,音乐学是以考证的扎实、资料的翔实而著称的。由于西方音乐汗牛充栋的文献积累,音乐学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一直非常风行。与音乐分析和民族音乐学相比,音乐学领域由于历史长、从事人员多,因而所发表的论著成果占压倒优势。
分析学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然而虽年青却势头兴旺。音乐作为最富内在逻辑的艺术门类,它的分析工具有可能比其他任何艺术都来得更为尖锐和有力。本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音乐分析方法层出不穷,力图探寻音乐结构的内部奥秘。令人感到兴趣的是,似乎与音乐分析这种专注于音乐内部结构的做法相平衡,民族音乐学的成熟则呼唤着对音乐的研究走向“外围”(虽然民族音乐学内部也一直存在着重音乐本体还是重文化背景的争吵)。而且民族音乐学由于其涵盖面的宽泛(它研究除西方艺术音乐以外的一切人类音乐文化),它对只限于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不啻是一种健康的调整。
这种“三足鼎立”式的格局是在实践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或多或少这种建构是在没有元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偶然形成的。因而这三者之间不仅研究的论域不同,也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和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三个子学科之间也没有建立足够的对话可能和相互联系。可以说,这三个学科背后的音乐观是迥然不同的。历史学将音乐当作一种受环境、历史、社会所制约或影响的人的创造物,它注意的是音乐如何沿革的线形关系,而可能忽略了音乐作品是超越时空、超越其当下环境、甚至超越作曲家主观意图的一种审美“自在”之物。分析则基本上是“反历史”的,它津津乐道于音乐内部结构的精密(有时近乎数学式)的考究,仅将作品当作一件固定存在于乐谱文本上的静态客体对象,而忘记了音乐作为一种音响艺术是与作曲家、演奏者和听众同时发生关系的一种动态结构物。民族音乐学试图将音乐放到它的整体文化环境中去考察,音乐不再是那种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而是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文化现象和体验方式。但是由于可以想见的困难,它却常常流于表层音乐现象及音乐在社会中的功能的简单描述。而且民族音乐学缺乏统一的“场”理论,使得它内部缺乏凝聚力而有失去“重心”的危险。
显然,西方音乐学的内部组织及构成也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也因此才会出现自我调整的欲望。但是,在考察这种自我调整之前,我们还要看看西方音乐学的这种摸式建构与西方的音乐生活有什么关系,以期能对它的形成有更深的理解。
美国著名音乐学家朗格(P.H.Lang)里程碑式的名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⑤的最后一章是“通往现代之路”,而它的最后一节名为“西方的衰落?”作者对二十世纪的展望显然是不乐观的。虽然他力图求得客观,但他的文字中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情调是无需否认的。调性解体造成了音乐形式内部的严重危机,精神上的虚弱使得音乐虚张声势、华而不实,现代社会的音乐会生活一方面助长了音乐的商品化趋势,另一方面也使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进一步割裂。而最为关键的是,工业社会“驱使人们脱离私生活走向集体主义,……一切从单一的,小的、个人的,质的,走向巨大的,普遍的,非个人的,量的,……人溶化在生活的巨大机器之中,在机器和官僚机关之中,在仅仅为了保证生存而作的努力之中,从而消灭了人的个性,从而走向消灭艺术创造”。⑥我们并没有从书中末页那试图高扬的略显空洞的语调中找到什么实质性的期望之光。
无独有偶。一位拿过音乐学博士头衔的现代大哲学家波普尔(C.Popper)在他的思想自传中直言,他觉得舒伯特是最后一个真正伟大的作曲家⑦(虽然他也喜欢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波普尔审美的趣味令人遗憾地太狭窄了,但是指责他不懂音乐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在此不拟考究这种悲观论调的真实度和本质根源。但是,它的存在是确实的。而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严肃音乐还能造就出一批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和勋伯格等这样的一流大师,五十年代之后的情形则更让人感到严峻。与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 “变革”不同,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音乐创作在观念上、语言上和思维上与传统的联系彻底被割断。1945年至六十年代为白热化的动荡时期,而之后又长期处于停滞期。不论是整体序列还是偶然音乐,它们最终都破坏了西方音乐上千年来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听觉关联感。音乐丧失了指向,每一音的意义不再通过它与其他音或整体结构的联系得来。它是孤立的,“自在”的。音乐创作不再作为一种审美创造而发生效应,更多它是作为一种哲学或观念突破或技法更新而获得价值。有的评论家认为这些现象均标志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艺术传统已告终结⑧。
于是,音乐内部的革命和突破反过来造成了自身的“异比”。严肃音乐创作的这种内在危机尤其表现在它不能达到风格上的“认同”,由此导致这种音乐丧失了交流的可能。作曲家在这种情形中的迷惑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听众对“新音乐” 的态度从早先的惊讶、愤怒或好奇逐渐变成了漠不关心。对现代音乐的排斥反映在音乐生活中,其具体表现为:(1)来自“左” 的方面:流行音乐以令人惊讶的绝对优势吸引了西方社会中的青年人,它的兴盛成为西方音乐生活历史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现象。(2)来自“右” 的方面:代表西方传统价值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对现代音乐持怀疑、观望态度,或者干脆全面否定。早在1955年,美国著名现代音乐评论家普利任兹(H.Pleasants)便出版了那本引起极大争议的小册子《现代音乐的困境》⑨。作者从社会学、历史沿革以及音乐语言、体裁、形式等各个角度全面攻击了现代音乐的理论和实践。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
音乐学正是这种对严肃音乐创作普遍感到悲观的气氛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种现象初看似乎荒谬,但却的确有自己的合理逻辑。艺术理论的发展与创作实践相互脱离在中外古今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学的关注中心本世纪以来一直以文艺复兴时期为焦点,旁及中世纪和巴洛克音乐。这种逃避现代创作的研究倾向一方面是由于悠远时代的大量音乐文献有待挖掘,但另外更主要的内在原因恐怕是音乐学者们都无法掩饰对现代音乐创作(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严肃创作)的深刻失望。他们或者热衷于早期音乐的现代复兴(由此引发本世纪以来兴盛未衰的历史演奏运动――historical performance);或者埋头于过去时代伟大音乐杰作的内部剖析以满足自己的审美乐趣(申克尔的分析体系背后隐藏着一种对 “过去好时光”不无遗憾的缅怀);或者他们将求知的长矛投向异国文化来扩大视野,从而获得对自身的一种批判(民族音乐学修正了西方对艺术、对音乐和对文化的根本看法)。的确,在所有具有世界性知名度的大音乐学家中,对现代音乐有特殊兴趣和偏好的人几乎是寥寥无几的,大约例外的只有威勒兹(E.Wellesz)、邓特(E・Dent)和达尔豪斯(C.Dahlhaus)。
和文学理论(批评)与美术批评(史)的发展轨道不同,音乐学在一种与当代创作实践相脱离的思路指导下走向了一条实证主义道路。由于对现代创作的失望产生了对音乐的审美判断的回避,也由于音乐审美评判实现在文字上的特殊困难,再加之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对音乐史学的重压,音乐学在整体上从一开始便缺乏“批评”――对艺术作品独特意义和价值的学术研究⑩。不错,实证性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避免接触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特质,音乐学(作为研究这门艺术的系统学科)无论如何是有缺陷的。它必须有所改变。而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
三、音乐学中的实证主义:战后的二十年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音乐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心” 的转移:德国学者一统天下的局面永远被打破了。英语国家成为音乐学研究的又一中心,而德语学者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移居他乡特别使美国获益非浅。当时活跃于音乐学界的第一流学者中很多人都先后定居、任教于美国。这些学者不仅给松散的美国大学音乐教育带来了严谨的德国式学风和规范,而且他们还造就了以后美国的音乐学的第二、等三代栋梁人物。在美国当时最知名的音乐学教授中,除了普林斯顿的施顿克(Q・Strunk)和纽约大学的里斯(G.Reese)外,其余的均是德奥裔学者:如阿培尔(W・Aeel)、布科夫策尔(M・Bukofzer)、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戈姆波希(O・Gombosi)、萨克斯、席莱德(L.Schrade)等等。而另一位巨匠朗格也是一位受欧洲教育的移民。在这些大师们的齐力努力下,美国音乐学的严格学院模式(它的特色是讨论班、博士论文和专题著作)为依托迅速得到了发展。五十年代,以里斯的《中世纪音乐》[11]和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为标志,美国音乐学开始成熟。至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国际音乐学界的地位得到了全面的巩固。
相比之下,英国的音乐学成熟较慢也较晚一些。由于英国人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他们对系统的音乐学术研究似乎总是持一种不自觉的怀疑态度。大学、学术机构对音乐学的支持是极为缓慢而被动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英国大学中所有的音乐教授只有一人称得上是真正的音乐学家――邓特(剑桥大学)。这种情况到了战后有了彻底的改观。1947年,三位重要的英国音乐学家被聘到大学任教:韦斯特拉普(J.A.Westrup)去牛津;刘易斯(A.Lewis)到伯明翰大学;亚伯拉罕(G.Abraham)在利物浦大学。同年,另一位将在英国音乐学界崭露头角的不同凡响的年轻人达尔特(T.Dart)也被聘到剑桥大学任讲师(1962年升教授).这四位学者被认为是战后英国音乐学的核心人物,其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英国的音乐学者受德国影响来得不如美国学者那么深远,他们似乎更偏重音乐学的实用性――高水平的音乐普及工作(BBC第三台的音乐节目质量之高是举世公认的)和音乐学与演奏的结合(仍是经验主义传统的遗迹;)。战后英国音乐学的重点工程是出版包括英国中世纪以来主要音乐作品的标准乐谱文本《大不列颠音乐丛书》(Musica Britannica)。以此为焦点,音乐学家展开了对乐谱资料来源、记谱法辨认、版本校对等一系列“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由于重视音乐的实际音响实现,英国音乐学家常常称音乐学的过程应该是从“音”开始(谱面的考证研究),以“音”结束(乐谱的实际演奏)。而英国学者也的确时常兼学者和演奏家于一身。上面提到过的韦斯特拉普和刘易斯均是巴洛克时期歌剧的专门指挥家,而达尔特本人则首先的一位辉煌的羽管键琴(harpsichord)的演奏家。笔者在英期间的导师特罗韦尔教授(B.Trowell)也曾从长时间从事歌剧演出的艺术指导工作(他的研究领域为歌剧史)。英国这种学术与演奏相结合的特点使得英国的音乐学一直与音乐实践家及音乐爱好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正是由于有音乐学教育出来的高水平的听众支持,英国在早期音乐复兴运动中是卓有成效的。
美国与英国的音乐学虽然在兴趣指向、模式特点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在音乐学应坚持扎实的文本考据、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一点上,它们不约而同都是实证主义的,这不仅表现在英美音乐学的整体历史发展中,同时也体现在具体的观点表述和研究工作中。
1961年第八届国际音乐学大学在美国纽约召开是美国音乐学的瞩目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一致公认的标志。会上美国中年音乐学家的代表人物门德尔以《证据与解释》为题,针对近年来巴赫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提出了他对音乐历史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在论述音乐学家们为何研究音乐史时,他首先驳斥了研究历史是为了实用的庸俗主义观念与理论。门德尔援引英国现代哲学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原话,认为我们研究音乐史的动机如同从事其他科学工作一样,是因为有一种“了解事物的冲动热情”(pas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ings)在驱使着我们,我们不断地感到好奇和迷惑,因而我们本能地要求解决这些迷惑,虽然他提到了艺术史与研究政治史有所不同,但门德尔的论点中心并不是做出这个区别,而是试图用普通历史学的方法来界定音乐史的问题。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证据,如何在音乐史中前后逻辑地完成对事实的演绎或归纳解释,而不是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溶入对于个别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的评判和分析。
然而,音乐学家对莫扎特的“好奇”或兴趣显然是与政治史家对拿破仑的兴趣不同。我们对莫扎特感到兴趣,恐怕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音乐仍能对今天的我们“讲话”,仍对我们有现时的审美意义。而拿破仑吸引我们则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行为或思想对19世纪的欧洲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希望知道过去,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拿破仑。艺术品之所以不同于政治或社会事件就在于它一旦产生便可能超越产生它的环境和时代局限而成为一件“超历史”的独特个体。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这种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冲突是艺术史研究中最深刻的内在矛盾,音乐史如何可能既将一件伟大作品置于一个连续性的历史叙述框架中,另一方面又公正判断它作为审美个体的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独特性质?换句话说,音乐史如何可能既是“音乐” 史,而又是音乐的“历史”?在音乐史中,仅仅解释了一个作品或几个人物间的前后影响关系、因果联系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批评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和审美内部构造,而这恰恰是门德尔的著名文章所没有提及的。在当时英美音乐学界实证主义的实践兴盛之时,可以理解,门德尔对这种实践的将理论概括也只能是实证主义式的。
两年之后,“美国的人文科学”丛书之一的《音乐学》作为美国音乐学成熟后的第一次自我审视引起了西方音乐学者的普遍关注。此书的中心部分“美国对西方音乐的学术研究”是由美国战后年青一代的音乐学家代表人物帕里斯卡写定的。其中所透露的实证主义气息也十分强烈。他客观地综述了美国音乐学的发展模式和现状,并全面概括了美国音乐的成就。在讲述美国音乐学家的研究领域时,他承认对于文艺复兴音乐的研究是美国音乐学的中心。以此为轴心,以中世纪和巴洛克两个断代的音乐为两翼,美国音乐学的天平几十年非常明显地倒向所谓“早期音乐”一边,另一方面,占现时音乐生活绝大部分的古典派和浪漫派音乐却基本上被忽略了,而现代音乐几乎无人做严肃的学术研究,在举美国音乐学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时,综合性的史论著作提及并不多,而绝大部分的篇幅让给了各种各样的“critical text”(批评文本)――标准乐谱文本,这无疑并不是由于作者的偏见所致,而是美国音乐学的实际情况的正常反映。在这种以编订标准乐谱文本(尤其是早期音乐的文本)为中心的实证性音乐历史研究中,所强调的是对“事实”(fact)和“证据”(evidence)的寻找,而不是对它们的解释,而即使有解释也至多只是历史性的因果、联系解释,而不是释义性的审美性的价值判断和批评研究。
虽然在美国的老辈音乐学家中有广阔兴趣的人并不少见,如戈姆波希对音乐中的节奏讨论的独到见解,布考夫策尔清晰的历史概括能力,朗格、萨克斯等人对文化史的开拓等等。但是对后代人更具决定性影响的是里斯的的两本巨头著作;《中世纪的音乐》和《文艺复兴的音乐》[12]。而这两本至今仍被认为是各自领域内的权威标准著作正是以严密、扎实的实证工作闻名。里斯在这两本专著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化能量囊括了到写书时为止的各自领域的全部文献信息,并以罕有的大师手笔将这些相互冲突或互不相干的资料内容统摄于富于逻辑的历史叙述中,至今西方音乐学著作中仍无出其右者。然而,这种或许只有“天才”才能胜任的不加选择全面吸收的研究方法到了初出茅庐的生手或能力较差的人的手中,其结果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里斯一方面为美国音乐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做出了无可否认的贡献,但他也不自觉地助长了美国音乐学中的实证主义的倾向。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尤其在五十年代西方音乐学的一个重大工程――新巴赫全集编订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巴赫协会出版了巴赫全集(1855―1899)后,由于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这套老版本中所存在的错误和不足便越来越明显。1954年,由德国学者丢尔(A. Durr)和达德尔受(G.V. Dadelseu)牵头,组织全世界的巴赫学者们共同重新整理编订新巴赫全集。对这位举足轻重的大作曲家的研究,西方学者所投入的精力和财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极其令人难忘的。恐怕文学中的莎翁也未得到过如此艰深精密的考据式研究。巴赫的每一个残存的手稿或抄本都被追查了;手抄稿的抄写人大多被查实了姓名;对手稿或抄本的纸张、墨迹和装订进行了现代化的科学分析;巴赫自己的谱面书写手迹被用来作为考察作品所属风格演化阶段的凭据。这种研究的结果可以说是相当辉煌的:巴赫作品的年代顺序被彻底订正了。尤其在声乐作品中,新的年代日期确定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现在甚至知道《农民康塔塔》的完成日期是1742年9月5日!此外,对原始资料的追踪还导致了对巴赫某些作品真伪问题的定论性发现,有些原先被认为是巴赫所作的作品现在被“清除”了出去。总之,我们手中的新巴赫版本是一个更为“真实可*”的巴赫了。
然而,在如此辉煌的实证成果面前,音乐学家却没有将研究推向深人――进一步探寻巴赫的风格本质和审美特质,巴赫作品的编年表被改变了,但仅此而已。而这种情形的改变要到六十年代以后了。
在音乐史学的实证研究中,只承认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才是证据,它排斥想象、假设、审美和洞察,而一旦外部证据不充足或不可能找全时,便陷于无措。它的思维在最好的时候是寻找作曲家之间、流派与流派之间的风格影响与联系,而不企求其他。音乐史由于对象是音乐,审美经验不可能不参与到它的研究中。归根到底,在音乐史中历史学家(作为学者进行客观研究)与音乐家(作为审美个体进行价值判断)是不可分割的。音乐学必须走向历史与批评的合二为一。
四、音乐内部结构的探询:理论和分析
既然弥漫在美国战后音乐历史学中的实证主义是一种时代的症候,那么它也不可能不表现在音乐学术探讨的其他方面:音乐理论与分析。
和国内一般流行的“音乐理论=音乐学=音乐学术研究” 的观念相比,西方对“音乐理论” 的理解似乎比国人狭窄一些。虽然在早些时候,“理论”的内容是更为宽泛的,但到了二十世纪,“理论” 的研究对象便特指音乐的各结构要素及这些要素如何结合的法则[13]。可以说,它相当于语言学中的语法学,本身即带有很大的“科学实证”的特点。理论的任务是发现或制定音乐语法法则。因此,本世纪前的许多理论(甚至也包括本世纪内产生的理论――即兴德米特体系)都企图寻找到或制定出一些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来。然而,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透视镜前回望考察这些理论时,却发现它们无一不与当时的音乐实践问题紧密相关。它们受制于本身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要解决的也都是当时音乐实践中出现的棘手间题。因而,西方音乐理论在发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热点” 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古希腊的音阶、调式理论;中世纪热衷于记港法理论的探讨;文艺复兴的兴趣转向音程结合的谐和理论及对位的方法;十八世纪是音乐修辞学理论与和声理论的丰收年代;十九世纪则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美学文献和曲式学理论。
二十世纪的理论当然不例外,它也关心着自己时代的突出问题。但是什么是本世纪音乐中的关键问题呢?
众所周知,功能调性和声的解体、调性向心力的丧失造成了作品内部凝聚力的涣散。因此音乐如何结构、如何组织成了作曲家要考虑的焦点问题。从某一角度说,整部二十世纪音乐史就是各个作曲家对这个问题做出不同回答的历史。理论上的反应同样如此,它研究和探讨的焦点正是音乐的形式-结构问题。音乐是如何“运作”(work)的?音乐的各因素是怎样组合的?作品获得内在统一的机制和秘密是什么?音乐是怎样通过分节、连续最终达到一个有机形式的?用最通俗的话讲,音乐是如何从第一个音走到最后一个音的?
如果本世纪的作曲家一般热衷于创立新的形式法则 (勋伯格、梅西安),那么理论家则对过去音乐中的内在结构奥秘更感兴趣。或许他们与音乐学家同样对现代音乐感到失望,因此他们用过去古典伟大音乐的“秩序”来反衬现代音乐的“混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理论” 的一个特别分支的“分析”(analysis)真正成熟了起来。
“分析”顾名思义,旨在对音乐结构的解剖。观察和描述。它与“理论”的关系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属于“理论”内的一个子学科,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一个自足的领域,与音乐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实际上理论与分析不是那么容易分得开的。分析往往要在某个理论体系指导下才能进行,而理论家与分析家也经常同是一人。本世纪上半叶最出名的例予大约是申克尔(H・Schenker)。
在西方,学者们有一个基本上统一的看法,即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最杰出的分析家有两个人:奥地利的申克尔和英国的托维(D. F. Tovey)。他们在理论-美学上都表现为彻底的传统保守主义,所涉及的曲目均是已在保留曲目中牢固建立了地位的作品,而且几乎都是纯器乐作品。但是,除此之外,两人在分析方法上和表述风格上的差别是极大的:申克尔注重深层结构,托维强调听者的直接感性反应;申克尔试图消除“笨拙”的文字描述方法,托维却以生动而流畅的散文批评著称。可以说,申克尔代表了条顿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沉的理性精神,而托维则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人[15]。
申克尔在世时很少为人所知,他的理论及分析在当时也没有多大影响。而托维生前却是英国音乐界的著名人物。然而,历史似乎与他们开了玩笑:在音乐学领域实证主义的浪潮流行时,托维的声望逐渐被申克尔压倒了。很显然,申克尔的“深层结构” 比托维的“小节→小节”的分析更富有逻辑,他的“图表-音符表达法”也比托维的文字更具有严谨、科学的优点。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二次大战后,申克尔的分析方法为什么会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得到普遍复兴。
申克尔对音乐结构的一整套理论称得上是西方音乐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对经典作品中的统一与逻辑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艰苦思索,认为伟大作品的内在秘密和意义不在音乐之外,而就在结构之中。不能否认,申克尔体系有很多优点。它关心的是音乐作品的各部分、各因素是怎样统一在整体框架之中的。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立体考察方法,它显然超越了以往曲式分析中只着眼部分与部分、因素与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的平面“线型”思维方式。申克尔的大范围的调性凝聚力观念、层面分割法和投射延长观念均是前人所未意识到而确实具有很大说服力的创造[16]。
然而,也许正因为申克尔体系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个人创造,它带有很大的独断性和僵化特征。当战后申克尔体系在欧美重新抬头之后,人们一方面承认这种清晰、逻辑的分析方法把握音乐总体结构的出色能力,但另一方面又不满它的狭窄和僵硬,逐渐开始在继承中进行了批判。
总的米说,对申克尔体系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上:
(1)这种体系在分析中倾向于忽略在听觉上给人以突出印象的细节特征。由于申克尔分析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简化技巧找出所谓的“原始线”(Urlinie)和“原始结构”(Ursatz),因而很多关键的细节,如某个休止、某个突出的力度转换,在分析中便丧失了应有的地位。与此相关的是,任何作品分析到最后,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这显然很荒谬。
(2)申克尔体系中没有考虑节奏,这恐怕是申克尔体系中最致命的一个弱点。在申克尔的分析中,对快乐章与慢乐章不加区别,节奏组织也无关紧要。而如果要透彻地理解一个作品,有乐在时间上的结构(即节奏)对音乐整体结构的影响是不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
(3)申克尔体系缺乏历史意识。且不谈他的分析中完全排斥调性前(pretonal)和非调性(atonal)的音乐,即使他对调性音乐的分析也犯了一个和以往理论家一样的通病,即他误以为自己探寻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客观真理:主三和弦对调性音乐的绝对统治。他恰恰忘了调性音乐本身有三百年历史,调性观念在历史中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4)由于过度强调音高的组织结构,使得其他因素无法移入。申克尔曾宣称,贝多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有结构(实际上只是音高结构)的严密逻辑和大范围的调性控制。从某种意义上,他并没有错。但是他过于“纯音乐” 了,以致于“纯”到根本不去考虑布局、平衡、戏剧性的动力气息等等在贝多芬音乐中极为重要的风格方面,更不要说涉及古典时期的共性语言和精神特质等更大的题目了。也正是因为由于同一原因,申克尔对歌剧等非“纯音乐”的品种体裁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的[17]。
虽然申克尔体系自产生影响之日起便遭到不断的攻击和批评,但即使对申克尔体系的整体概念持否定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能从中学到许多。在纷争中,对申克尔体系的改造和扩展越来越成为理论家、分析家关注的中心。人们试图从各个方面发展申克尔体系的“潜能”,并弥补它的缺陷。在这个过程中,结果是不平衡的。也许最令人满意的成就是在扩展申克尔体系的适用范围这个方面。萨尔策(F.Salzer)与福特(A.Forte)走两个最突出的人物[18]。尤其福特对非调性现代音乐的分析现今已基本自成体系。但是,在节奏的理论方面,申克尔体系的改造进展甚微。虽然库泊尔(G.Cooper)和梅耶尔(L.B.Meyer)于1960年出版了《音乐的节奏结构》[19]一书,但书中所提出的节奏理论和分析方法并没有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进入六十年代后,音乐分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日趋活跃。学者们不仅继续对申克尔体系进行挖潜改造,而且也开始扩大视野,拓展新的疆界。信息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新兴学科、技术向音乐分析一次又一次地发起挑战。英国从来对申克尔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在那里,以凯勒(H・Keller)和沃克(A.Walker)为代表,动机、主题、“前景” 的细节一直是分析家的注意焦点。传统的音乐历史学也不断地吸收音乐分析的成果,并要求与音乐分析相结合。托维又被人重新想起,并给予重视。虽然申克尔体系在这种纷乱多样的局面中仍是一支强劲有力的主旋律,但不可否认的是,音乐分析也走出了“就音论音” 的实证主义阶段,它希望用历史深化自己,并企图对审美理解有所贡献。可以说,有些分析著述和文章已经是“准批评”―一通过对个别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和描述,达到对该作品独特意义、审美价值的深入理解。
五、音乐学重新调整:走向批评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概观” 中,我已迅速浏览了六十年代至今席卷音乐学界的反思浪潮的主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传统的音乐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和抨击,而逐渐趋于衰落。首先,整个普通历史学界由于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的不满而引发了对“新史学” 的呼唤,这当然会影响到音乐历史学;其次,文学(及美术)理论界长期以来的批评传统使音乐学界相形见拙,这促使音乐学界反思自己;再者,由于音乐分析的影响,音乐学的注意力开始从“文本问题”、“真伪问题”转向音乐的理解和评判。
音乐学在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重新调整时,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这种“元理论”(理论的理论)的热烈讨论是一门学科“自我意识”苏醒的健康标志。在这场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克尔曼(J・Kerman)和特莱特勒(L.Treitler)。
克尔曼的成名之作是《作为戏剧的歌剧》[20]。书中结合了歌剧史和戏剧批评两个历来各自分割独立的领域。由于此书对歌剧审美本质和价值评判的大胆论述和尖锐的看法,这本书一直是歌剧方面学术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克尔曼本人一直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反对干枯的考证和自许为“科学” 的所谓客观精神,这种态度最充分地表露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美国音乐学侧影》(1956年)一文中。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21]中,克尔曼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美国音乐学战后以来发展趋势的正面批评。他对照文学研究和美术史的研究,对音乐学家只关注目录、手稿以及文本(谱面)分析大为不满。在姐妹艺术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是批评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艺术史不同于普通历史。音乐研究的目的应是提供音乐作品的“上下文”背景(contextual background),以帮助人们达到对具体艺术作品的深层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音乐学应向批评*拢。
英美音乐学界对克尔曼批评的反映是热烈的。人们认为克尔曼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有真正学术意义、有讨论价值的重大问题。而关于音乐学研究的目的、价值导向、方法等等“元理论”的讨论也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克尔曼的论点不是没有人反对,但他对英美学术界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尤其是克尔曼不但在口头上提倡批评,而且还用自己的具体研究成果做出表率,这使他的贡献更为突出[22]。
几乎与克尔曼同时,一位中世纪音乐的学者特莱特勒也开始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音乐学的现状进行重新审视[23]。他的声音不如克尔曼尖锐,但是比克尔曼更加深刻和稳健。这是一位受过良好哲学训练、并且有着广泛涉猎的音乐学家。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断地涉及狄尔泰、德罗伊森(Droysen)、克罗齐、科林伍德等著名历史哲学家的观点,并在一些具体的艺术史问题上超越了他们。因果论、决定论的(音乐史是由前因后果联系起未的事件、作品和人物序列)和进化论的(将音乐史看成是不断由初及盛、从盛至衰的有机生长过程)音乐史观都遭到了他的抨击。特莱特勒认为,最有价值的历史学解释并不是对事件原因、结果的解释,而是关于事件特质、特性的说明;历史学家区别于他人的并不是他的对象――过去的事件,而是他在处理自己对象时所持的态度和所采用的方法,即,在事件的“整体上下文”(total context)中寻找事件的原因和意义;音乐作品在历史中不应只被当作整体过程中的一个链环,而应以“物自体”(as a thing in itself)出现,它在历史当中,但又超越历史;音乐作品应不断地由后人做出新的释义,这是后人的文化责任,也是伟大作品生命长在的内在秘密。特莱特勒还撰文探讨了历史学、分析与批评之间的关系及相互、结合的可能,这都为英美音乐学的重新调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英美音乐学对“元理论” 的讨论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已提到过,德语国家从没有丧失过对纯理论的爱好。1983年,英国翻译出版了当代西德的音乐学大师达尔豪斯(C.Dahlhaus)的著作《音乐史基础》[24],书评界认为这是当年英美音乐学出版界的重大事件。这本只有一百余页的薄薄的小册子影响还在不断深入、扩大。虽然达尔豪斯是相当折衷的学者,但他强调,历史不能与审美脱离,也无法与之相脱离。音乐史需要完成双重任务:对过去的音乐作品的渊源、发展和影响进行描述(历史叙述),以及揭示现在听者与过去音乐作品的关系(审美观照)。他坚持音乐史的自律性,反对将音乐史置于文化史、思想观念史的统帅之下。在如何解决历史的连续性和审美的直接性(immediacy) 这对突出的矛盾时,他的观点是极富启发的:应在具体作品中看到历史的积淀(不仅有作品的“前历史”,还应有作品产生之后人们对它不断做出解释的“后历史”),而不应把作品仅当作历史演进中的一环或“时代精神” 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有见地的思想。很清楚,达尔豪斯提倡的正是一种历史学与审美的统一,一种以批评为主导的新型音乐史学。
让我们暂时离开纯思辨的元理论领域,看看在实证主义不断遭到抨击的年代里西方音乐学家具体做了些什么工作。当然,实证主义式的研究工作一直在继续,而且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帮助,文献、资料方面的工作更加扎实和科学化。但是,四、五十年代那种为实证而实证,只问事实不管评判的的主导方向确实改变了,最明显的例于是对于贝多芬的研究。
贝多芬研究自六十年代末至今仍是一个非常“热” 的领域。它的重心不在成形的乐谱定本上,而在作为作品雏型的“草稿”(Sketch)上。历史上的大作曲家中也许贝多芬是第一个创作前事先要做大量草拟的人。而幸运的是,这些草稿绝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这批极有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文献。他们首先对分散在各处的草稿进行汇总,经过艰苦、细致的考证后,将它们整理、分类和编目,这种实证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比之五十年代的巴赫研究可以说并不逊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草稿研究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上走向了深入。比如,温特尔(R.Winter)发现,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 131有五个完全不同的整体框架构思。他考察了贝多芬这些有关各个乐章间组织平衡的草稿的原始意图,追踪了贝多芬如何在构思中提出的问题、并找到满息的解决方案[25]。又如金德尔曼(W.Kinderman)对迪亚贝利变奏曲op.120的研究。他从草稿中发现贝多芬1819年时便正接近完成全曲。但贝多芬突然辍笔,直到1821年才重又拣起这首“旧曲”,加进了新的变奏,使全曲的整体结构更加清晰、更有说服力[26]。在贝多芬草稿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两条略有区别的思维线索:其一,通过草稿研究,更进一步理解贝多芬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的心理;其二,旨在通过研究更好地理解特殊的、具体的作品的意义及特质。在最好的情况中,这些研究结合了考证、历史、分析与研究者的个人审美体验,变成了一种具有实证风格的学院式批评(academic criticism)。
引人注目的是,贝多芬草稿的研究带动了一系列的作曲家草稿、手稿研究。贝多芬草稿研究成了音乐学新发展的一个样板。海顿 莫扎特、门德尔松。肖邦。柏辽兹、勃拉姆斯、威尔第、马勒、布鲁克纳、德彪西等等大作曲家的名字开始在学术刊物上更加频繁地出现。英美音乐学界原来那种以巴洛克之前的音乐学为中心的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原来在五十年代完全被忽视的十九世纪得到了重视,而且对二十世纪的音乐也不再是现象罗列和情况介绍,开始用历史的眼光和敏锐的分析做出深刻的批评。当然,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早期音乐的实证工作正基本上告一段落。此外,十九世纪(以及本世纪上半叶)已经逐渐在变为遥远的过去,学者们已经有了研究中所必须具有的历史透视。
与英美音乐学界同步,德国也兴起了十九世纪的研究高潮。前一节提到过的卡尔・达尔豪斯是其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本人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著斯坦・德普雷(Josquin des Pre)的,但六十年代后转向十九、二十世纪,尤其以瓦格纳为研究中心。由他主编的“十九世纪音乐史研究丛书”(Studien zur Muslkgeschlchlchtedes 19. Jahrhundert,1965一)是德语世界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至今已出到六十余卷。这套丛书中的论文集或专著遍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不仅包括十几世纪音乐观念的清理、贝多芬身后的接受史,而且也涉及所谓“庸俗音乐”(trivial music)的流传情况和社会学研究、欧洲之外的非西方音乐文化。达尔豪斯此人近来也非常受到英语世界的广泛注意,他在历史、美学、旋律理论、和声理论、节奏理论、分析、批评、当代音乐等诸多方面均有著述,人们惊异他能够将如此广泛的兴趣和渊博的知识与深刻的思辨熔于一炉。从1979年开始,英美正连续翻译出版了他的七本著作,这在英美音乐学史上是极罕见的。
看来,十九世纪已成了整个现在西方音乐学的又一个重要的焦点领域。由于十九世纪音乐与普通听众的关系最为密切,音乐学对大众的音乐教育也在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就音乐学自身而言,由于同分析等其他学科不断进行结合(分析原来的重心就是十九世纪音乐)因而正在走向更加全面、更加综合的批评。
在这一部分结束之前,我还想特别提到两位人物。他们不属于正统的音乐学家,但是他们的研究著述都在英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代表了当今英美音乐学的最新的健康走向。
梅耶尔(L.B.Meyer,注意不要与东德的音乐学家。作曲家E.N.Meyer相混)在美国是以音乐美学家的身份出现的,这有点不寻常,因为在英美,音乐美学基本上仍然是哲学的下属分支,音乐家并不十分关心。梅耶尔是一个视野非常开阔而思维又非常清晰的思想家。他的著述更多是面向大众,而不限于音乐学术小圈子。1956年出版的《音乐中的情感和意义》[27]一书使他一举成名。这部著作成功地调和了自律形式论和他律论的观点。作者从听者的感性经验出发(而不是从音乐本体出发),用心理学的术语重新审视了音乐意义的生成过程,而关于音乐意义的理论,作者又受到申克尔体系的极大启发。他认为,音乐必须在风格范畴中才能得到理解,离开具体的风格限定去空谈“意义、感情”是没有结果的。正是在由文化、风格所限定的常态规范内,听者才可能对音乐事项的连续和进行有一种期待(expectation),这种期待被满足,或被推迟、被阻滞便会引发一系列不同的意义和感情。梅耶尔的理论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方法,以审美知觉、审美经验和审美过程为中心,因而避免了通常音乐失学讨论中那种玄而又玄、不着边际的空谈,得出了富有意义的结论。而且,他的学说溶进了历史透视和文化类型的区别,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地域的音乐,这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因此,梅耶尔的观点受到了包括民族音乐学家在内的普遍欢迎。
梅耶尔后来又进一步完善和扩展了自己的学说。在《音乐、艺术与观念》[28]这本书中,他用新发展起来的信息论和控制论学说重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使之立于更加严密和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在这本副题为“二十世纪文化的模式与导向”的史论著作中,他用自己原有的美学理论检查了二十世纪的复杂文化现象(尤其是音乐),深刻地指出,五十年代后的音乐现象标志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音乐传统的终结。在不远的将米,将是形式主义、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和传统主义多元并存的动态平衡,“大师”“音乐的永恒”将不再是共认的判断标准。这是一本思维多于事实、抽象多于实证的著作,已被公认是关于二十世纪后半叶音乐文化的重要专著之一。1973年,梅耶尔出版了他的第四本著作《解释音乐》[29]。此书是理论、分析和批评的混合物。作者探索了将自己的美学理论扎实地落实到具体作品分析上的可能性,不仅重视逻辑的深层结构,同时也不忽视“前景” 的感性细节。书中对申克尔分析的创造性运用既可以是申克尔体系的扩展,也可以说是对申克尔的扬弃。
另一位异军突起的人物是罗森(C.Rosen)。比起梅耶尔,他更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怪杰。这位以钢琴独奏为职业的法语文学博士(!)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写下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30]。翌年(即1972年)此书获得了美国国家文学艺术书籍奖,美国音乐学协会组织了专门会议讨论此书。说来奇怪,“古典主义时期” 这个在音乐史上似乎最为人所熟悉的断代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标准专著。罗森这本著作是对这个空缺的一个重要填充。虽然《古典风格》不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历史著作(罗森进行了很大的选择,略去了“小人物”,也略去了很多的重要作品),但是罗森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分析和广博的知识为理解这个时代的音乐语言提供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样本。他的引文既没有“时代背景”、文化氛围”之类的玄妙话,也没有斤斤计较于数据、事实的枯燥考证。他的角度是演奏者的角度,是听者、接受者的角度。他的文风师承了托维,但又超越了托维。这是一本审美批评的著作,是一本寓历史于具体作品、寓理性知识于感性判断、寓情感内容于材料结构的真正音乐批评。
六、尾声和结语
从上述情况看,西方音乐学那种“历史学、分析、民族音乐学三足鼎立” 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历史;美学、分析和批评不可避免地而且也应该走向综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音乐学自身也发生着变化,它同西方艺术音乐研究的关系也重新调整。
五、六十年代,以梅里亚姆(A.Merriam)等民族音乐学家为代表,呼吁将一切音乐现象置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研究西方音乐的学者们出于对以前音乐学那种只管音符、不问其他的实证主义的倾向不满,也纷纷要求音乐学全面*向民族音乐学,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重新考察西方音乐。但是,最近以来,以胡德(M.Hood)为代表的另一派民族音乐学家的观点却逐渐占了上风。他们反对用“文化”、“社会“淹没音乐本体,主张音乐自身和音乐所处的文化环境必须同时并重。尤其胡德坚持民族音乐家必须参与所研究的音乐,真正从感性上了解音乐。
人们察觉到,民族音乐学原有的“田野――案头” 的工作方法在处理无文字、无历史的原始部落音乐时相当奏效,但在研究具有自身历史发展的非西方音乐文化(如中国、印度)时却显得不足。另一方面,西方音乐的文化的上下文与非西方音乐也完全不同,套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并不能保证成功。其结果,不是研究西方音乐的音乐学*向民族音乐学,而是两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西方艺术音乐研究保持着原来以音乐为本的特色,同时又扩大了文化的维度;而民族音乐学也在强调音乐的文化角色的同时,更加注重音乐本身的历史沿革、风格变异以至于它的审美特征。美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西格尔(C.Seeger)一生追求包纳整体音乐学的统一场论(unified theory of musicology),这种理想看来正在趋于实现。
这篇冗长而又“蜻蜒点水” 式的掠影也该就此打住了。“知彼” 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好奇和求知,更重要是为了“促己”。西方音乐学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让人难忘的。它有缺陷,但生机勃勃。它是在几代学者的坚实工作中逐渐成长的,如今音乐学已成了一座完整而坚固的学术大厦。至今为止,连文学界和美术界也没有能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相对等的学术大工程,西方音乐学者所作的一切应该说许多方面是值得借鉴的,面对西方音乐学的挑战,我常常想,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实在很多,这些问题诸如:中国音乐学应该从何发展?怎样发展?西学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战略重点究竟应该是什么?音乐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应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与音乐的创作、演奏(唱)实践又应是一种什么关系?音乐学在我国的音乐生活和音乐教育中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音乐学家的培养怎样才是合理的?等等,这样的问题几乎可以一直提下去。而要回答它们则必须依*全体音乐学者们的聪明才智。在讨论和争论中,我们也许会达成某种共识并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稳步地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
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搞学问。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立志深下功夫,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我们不要总是陷于自卑沮丧或浮躁自大的两个极端中。学术需要一种执着而又虚心的辩证精神。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我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1989.7.7.于沪
注释
①“Evidence and Explanation”Report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Musicology Society Congress NewYork,1961, P.3
② Musicology,Princeton Uni. Pr.,1963
③‘A Profile for American Musicology” ”Journal of American Musicology Society” (1965),61
④十九世记德国历史学界风行的兰克(L. Ranke)的实证主义方法无疑极大地影响了音乐学的早期形成与发展,限于为篇幅.本文在此略而不提.
⑤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1941.我国有此书最后一部分的中译本(张洪岛译),更名为《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
⑥《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P.393―394.
⑦《无穷的探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P.53.
⑧ L. B. Meyer, Music,the Arts and Ideas, Chicago Uni. Pr. 1967, P.68
⑨ The Agony of Modern Music, New York, 1955
⑩我国音乐学界对“批评”的理解与西方音乐学界相比有很大不同.笔者拟另做专文论述。
[11] Music in the Middle Age,New York, 1940
[12] Music in Renaissance,New York,1958
[13]参见《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下简称“新格罗夫”)第18卷,P.741,“Theory,theorists”.
[14]参见“新格罗夫”,第1卷,P.340,“Analysis”这个长条被认为是“新格罗夫”中非常出色的一个条目,是英语文献中第一次对“分析”全面的综合阐述。
[15]托维的分析国内有少许介绍,参见陈登颐所译的 《交响音乐分析》(第二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16]国内对申克尔的介绍评述请参见:周勤如”音乐深层结构的简化还原分析”,《音乐研究》1987年第2期于苏贤“申克尔体系概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二期。
[17]参见E. Narmour, Beyond Schenkerism, Chicago,1977.这是最新见到的一本全面攻击申克尔体系的著作,影响颇大。
[18]参见F.Salzer, Structural Hearing, New York 2nd ed.,1962;A. Forte, Contemporary Tonal Structures,New York,1955;A.Forte, The Structure of Atonal Music,New Haven and London,1973
[19] The Rhythmic structure of Music,Chicago, 1960
[20]J. Kerman:Opera as Drama , New York,1956
[21]参见本文中第二部分的注释。
[22]参见他的The Beethoven Quartets,New York and London,1967.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贝多芬批评著作。
[23]特莱特勒最重要的文章是:“Music Analysis in an Historical Context”,College Music Symposium vi(1966),P75;”On Historical Criticism”,Musical Quarterly, Iiii(1967),P188;“Historiography,Criticism and Beethoven’s Ninth symphony”19th Century Music Spring 1984.P.1
[24] Foundations of Music History,Cambridge,1983。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中蒋一民同志撰有《音乐史学的美学化》一文介绍此书(不过笔者对该文中的一些观点持保留态度)。
[25]“Plans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String Quartet in C Sharp minor”,Beethoven Studies 2, London,1977
[26]“New Lights on Diabelli Variations op.120” Journal of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Summer1982
[27]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Chicago,1956
[28]Music,the Arts,and Ideas,Chicago,1967
[29]Explaining Music,Chicago,1973.梅耶尔的第三本著作见注①.
[30] The Classical Style,New York,1971,2nd ed.,1972
此文发表在《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1期
上一篇: 《图尔内弥撒》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
下一篇: 返回列表
【相关文章】
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